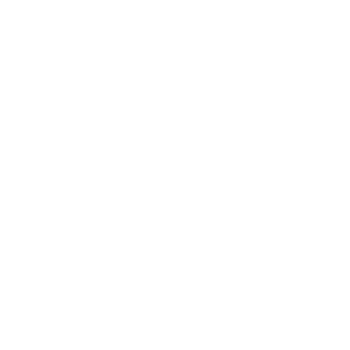我朋友華生雖然想法不多,僅有的想法卻都頑固得出奇。長期以來,他一直在苦苦糾纏,逼着我自己寫一篇講述以往經歷的文字。這興許是我自討苦吃,因為我經常都得指出他的毛病,說他寫的那些故事如何如何膚淺,還說他只知道迎合大眾的口味、不懂得嚴格地遵循事實和數據。「你自個兒試試好了,福爾摩斯!」這就是他的反駁。不容否認的是,提起筆來之後,我自己確實有所體會,既然是寫故事,那就必須寫成讀者愛看的樣子。下面這個案子讀者肯定愛看,因為它是我那份記錄當中最離奇的案子之一,只不過碰巧被華生漏掉了而已。既然說到了我這位老朋友兼傳記作者,我不妨借機補充一點,偵辦各種區區小案的時候,我之所以要不辭辛苦地拖上一名同伴,並不是因為我感情用事,也不是因為我突發奇想,而是因為華生確實有他的獨到之處,只不過他性情謙退,光顧着過甚其詞地吹捧我的事跡,沒有留意到他自己的優點。如果你的同伴能夠預見你的結論和行動方略,那樣的同伴只能說是非常危險,反過來,如果他自始至終都對事態的變化感到驚詫莫名、自始至終都對未來一片茫然,那倒可以算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理想助手。
按照我記事本裏的記錄,詹姆斯‧M. 多德先生登門造訪的時間是一九零三年一月,也就是布爾戰爭剛剛打完的時候。多德先生是一位魁梧挺拔、朝氣蓬勃的英國公民,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那陣子,華生老兄已經做下了我記憶之中唯一的一件只顧自己不顧交情的勾當,拋下我去討了一個老婆。多德先生上門的時候,屋裏只有我一個人。
我的習慣是自己坐在背對窗子的位置,把我對面的椅子留給客人,好讓他們完全暴露在天光之下。詹姆斯‧M. 多德先生似乎是不知道怎麼開口,而我也沒有幫助他打破沉默,原因是我可以趁此機會多觀察他一會兒。我早就已經發現,明智的做法是一上來就讓主顧領教一下我的本事,到這會兒,我便把一部分的觀察結論說了出來。
「據我看,先生,您一定是從南非回來的。」
「是的,先生,」他多少有點兒詫異地回答道。
「以前是在帝國義勇騎兵部隊,應該沒錯。」
「沒錯。」
「米德爾塞克斯義勇騎兵團,毫無疑問。」
「確實是這樣。福爾摩斯先生,您簡直跟巫師一樣靈啊。」
看到他迷惑不解的表情,我不由得笑了起來。
「一位英武的先生走進我的房間,臉上帶着英國太陽曬不出的那種黝黑顏色,手帕又塞在袖子裏、沒有揣進口袋,看到這些情況,這位先生來自何方並不是一個很難推測的問題。